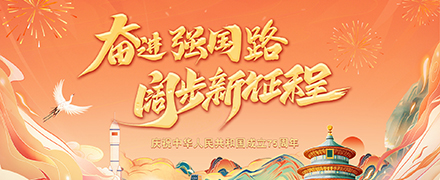“回望我这一生,每一个足迹都浸透着党和军队的恩泽。”96岁的孙思明说。
微微佝偻着脊背,这位八路军老战士像一株饱经霜雪的古松,每挪一步都似在丈量岁月的厚度。枯竹般的手指虽有些发颤,却执着又热情地攥着记者的手,指节里仍蕴藏着当年紧握步枪的力道。
1929年11月,孙思明出生在山东临朐一个贫苦农民家中。“上到小学五年级,鬼子来了就没法再上学了。”他说,他的人生轨迹也由此改变。
临朐地处鲁中山区,因地理优势,抗战爆发后成为八路军及抗日武装的重要活动区域。日军在这里制造过多起惨绝人寰的屠杀。
亲眼目睹日军的暴行后,孙思明毅然选择参军报国,成为一名八路军战士。
他至今仍清晰记得,那一天“是1944年3月1号,是我一生永远难忘的好日子”。
当时,已是儿童团员的孙思明和小伙伴们整齐地坐在草地上休息。一个穿着灰色军装的大个子走到他们面前,拿着小本子开始点名。点到他的名字时,他马上站起来立正答到。
大个子问:“愿意参加八路军打鬼子吗?”
他大声地回:“我愿意!”
从此,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孙思明穿上粗布军装,从八路军山东纵队鲁中野战第一所的看护员做起,走上了一条以医道为枪的人生道路。
据老人介绍,当时看护员的主要工作是照顾前线负伤转运下来的伤员。
一次,日军对根据地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大“扫荡”。为防止出现意外,孙思明负责的伤员都被秘密转移到深山老林的山洞和堰墙洞里。他和一个民兵大哥、妇救会的一个大嫂共同照顾3个堰墙洞里藏着的伤员。
“一到两天就要巡诊一次,必须在夜间悄悄进行。”老人说。
白天,他们把巡诊需要的水、干粮以及医疗物资全部准备好,一到天黑就背起东西悄然出发。
“最远的堰墙洞有3里多山路,摸黑走起来很容易摔倒。”老人回忆,“我给伤员换药时,大嫂就在旁边拿蜡烛照明。每每看到伤员们的伤口化脓越来越严重,有的还因此发起了高烧,我们总是忍不住默默地掉眼泪。”老人说,可伤员们不管伤情有多重,在洞里的日子有多难熬,从不叫苦喊疼,从不落泪。
巡诊时还有条严格的纪律规定——从洞里拿出的所有垃圾特别是换药用的敷料,一律打包,谨慎处理,“绝不能随地乱丢”。
“严格规定的背后是惨痛的教训。”老人低沉地说,一次,因换药的敷料没有处理好,被日军发现,导致医务人员和伤员都惨遭杀害。
战争是残酷的。“由于日本鬼子的严密封锁,野战所的医疗物资严重匮乏。所里没有任何检查仪器,连体温表、血压计也没有。”老人回忆,敷料都是自己用白粗布裁剪制作的,消毒只能用老百姓的蒸笼蒸。
很多伤员因没能扛住伤情而牺牲了。
“他们都还很年轻,明明能端着枪去打鬼子,却倒在了缺少药品治疗的后方,太可惜了。”老人说着不停摆手,连连叹气。
除作战负伤的伤员,孙思明所在的野战所还陆续接收治疗一些在频繁作战的情况下,因卫生等条件差而患病的官兵。有些人感染了疥疮,有些因缺乏维生素A患上夜盲症,丧失了夜间与日军作战的能力。
孙思明印象最为深刻的是伤寒。这种病后期会导致死亡率较高的并发症肠穿孔。
“病人只能喝流食,不能吃硬食。”老人回忆,他当年护理过的一个病人,偷着吃了硬东西,最终造成肠穿孔牺牲了。
提及往事,孙思明仍心如刀割。
抗战胜利后,孙思明跟着部队南征北战,经历了淮海战役的炮火洗礼,边参加战斗边运输救护伤员。
在血与火的淬炼中他获得了成长——在枪林弹雨中学习包扎救护。战友的伤痛激发了他坚韧的意志,锻造了他救死扶伤的初心。
孙思明说,正是从那时起,他立志要把治病救人的本事学好练精,让更多的人消除疾患,远离病痛。
新中国成立后,孙思明系统学习医学知识,将战地救护实践与医学理论熔铸一身,成为一名技术精湛、信念坚定的人民军医,全身心投入到部队医疗工作中去,主研项目多次获军队科技进步奖。
“我就是想把当年缺医少药的苦,用手术刀刨掉!”这位老军医说。
在周围人看来,孙思明不仅是一名心怀大爱的医者,更是一位矢志不渝的传承者。
在熟悉他的医生朱大成眼里,孙思明离而不休,仍坚守医疗一线,以伏枥之志发挥余热20年,直到80岁才真正在家休养;倾力“传帮带”,热心指导年轻人;结合数十载临床经验及老年生理特点,编著实用养生手册,惠泽众人。
孙思明的老伴丛培芳是1948年投身革命洪流的一名老解放。在老伴眼里,丈夫尤为注重家风传承与后代教育,时常拿出珍藏的、带着硝烟印记的立功奖章和证书,向后辈讲述那段烽火岁月,讲述缺医少药的锥心之痛,教导他们要为国家为社会贡献力量。
今年是抗战胜利80周年。作为战争亲历者,孙思明说:“我就是要让家人、让一代代年轻人勿忘国耻,铭记历史。”
(新华社济南7月20日电)